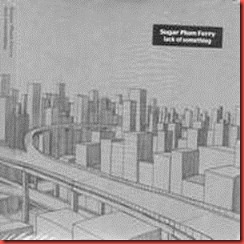在臺灣,觀眾所能看到的紀錄片題材,大概有下列幾種:
a. 社會議題紀錄片-創作者關心某個社會議題而產生的紀錄片。無論是災後重建、勞工議題、原住民族議題、核能問題、SARS與禽流感、死刑議題等等。創作者長期「蹲點」或是「跟拍」,透過紀錄片,創作者反映出自己的立場;
b. 國家地理頻道、Discovery 所放映的紀錄片。歷史、動物、世界知識....當然,臺灣也有人製作傳記類的紀錄片。
臺灣看得到的大概就是這兩類了。
以上這兩類紀錄片,觀眾其實都得不到「觀後愉悅感」,國家地理頻道與 Discovery 的紀錄片令觀眾得到的是一種「知識充滿」的感覺,還談不上「看完會開心」。而近年來,我看到會開心的紀錄片,有《青春啦啦隊》與《不老騎士》,那是因為那些高齡的老太太老先生,在鏡頭前面毫不扭捏,展現天真無邪的一面,他們認真生活的模式,鼓勵了所有觀眾。但無論如何,台灣的紀錄片製作模式,都脫離不了「跟拍」「蹲點」「社會議題」。這次看到了2013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《尋找甜祕客》,我覺得對台灣所有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,會是一項很重大的啟發。
首先,這個故事根本無法跟拍,無法蹲點。片中主角首次發片的時間,那年我才兩歲,這樣根本不會有任何動態畫面。歌曲流傳到南非是1991年,而主角首次受邀到南非演唱的時間點是1998 年,本片導演知道這個故事的時候,都已經是2008 年了。看到了嗎?這位紀錄片導演從不曾在事件現場出現過,導演也只是「聽說」了這個故事。如果導演決定要拍攝這個故事,那麼他面臨的風險大不大?素材夠不夠?
素材本身就是一個決定影片成功與否的要素,本片最強的素材應該就是音樂了,但是缺畫面,不過現在都可以用動畫、訪問、歷史畫面補齊。那麼需要哪些素材,怎麼處理影片結構,最後一整個事情就是「如何讓影片有強烈的說服力」。我相信本片的所有一切結構都是透過設計撰稿而得,首先說明南非的時空環境,然後兩個大粉絲出來說明主角有多紅,接著介紹他的製作人出場,他的女兒出場。就這麼樣抽絲剝繭般,總算最後是主角在家中,緩緩打開窗戶,本尊現身....
我忍不住「哇!」了一聲。主角還在!但我知道,這些都是「戲劇結構」。即便是主角在街頭緩步走路,在雪地裡走路,那都是設計過的。導演早就設計好一切的一切,導演早就去拜訪當事人好幾次。這樣的製作過程,我想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是很難想像到的。
我看完這部紀錄片,從戲院出來的時候,情緒是愉悅且開心的。我不是因為關心某個社會議題而去看了紀錄片,而導演的動機也只是「我想要告訴觀眾一個很棒的傳奇故事」,如此而已。倘若各位去查閱 2013 年奧斯卡所有入圍的紀錄片,除了「尋找甜祕客」之外,其他都帶有很深的社會議題色彩。我想「看完會快樂」這件事情影響了影藝學院的會員,對這部片奪魁肯定加分不少。
順帶我想要提及紀錄片當中的「作者論」與「社會議題」之間的關係。各位都知道麥可摩爾的紀錄片有很強烈的導演印記,即便他是搞社會議題,但反諷式的剪接手法變成是他最強烈的「導演印記」。2004 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片《戰爭迷霧》內容只是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國防部長做了25小時的訪問,然後剪成兩個小時,但表現手法有絕對的「作者方式」。可是台灣的紀錄片創作者都把「議題」放在作者之前;結果就變成「拍原住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」或是「拍災區的紀錄片導演」「拍新移民議題的紀錄片導演」。「作者標記」反而跟議題連結在一起。如果在沒有任何外界資訊之下跑去看某部臺灣紀錄片,首先可以從議題來猜猜看導演是誰,再來只好等到結束時候的字幕表,才會認識導演。所以,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,是否也能夠跳出自己擅長的議題,再多加強一些個人獨特的表現手法?
站在觀眾的立場,我衷心期待有更多「看了會開心」而且「有作者印記」的臺灣紀錄片;而站在「曾經是紀錄片導演」的立場,這當然也是我要努力的目標。在此把這部「尋找甜祕客」推薦給臺灣所有紀錄片工作者,各位都可以從此片當中找到紀錄片更廣的面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