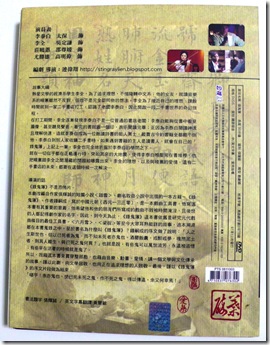註:此文為北京電影藝術雜誌專用稿,除敝人部落格外,任何人意欲轉載均需取得北京電影藝術雜誌同意。
試別人不敢試的-專訪魏德聖
時間: 2009/02/28 地點:台北市 果子電影公司辦公室
採訪、整理: 連偉翔
受訪者:魏德聖
1969 年生,台灣台南人
1989 年遠東工專畢業
1990 進入電視圈
1993 正式進入電影圈
個人作品暨得獎紀錄:
- 「賣冰的兒子」 1994優良電影劇本獎
- 《夕顏》 第十八屆(1995)金穗獎優等錄影帶
- 《對話三部》 第十九屆(1996)金穗獎優等短片,1998台北電影節「短片成年禮」單元
- 《黎明之前》 第二十屆(1997)金穗獎優等短片,1997比利時布魯塞爾影展優等短片
- 《七月天》 1998電影短片及紀錄長片輔導金補助 1999台灣第一屆純16獨立影展,1999台北電影節獨立創作競賽提名,1999溫哥華國際影展觀摩,2000金馬國際影展觀摩,2000韓國釜山國際影展觀摩
- 《賽德克.巴萊》2000優良電影劇本獎
- 「火焚之軀──西拉雅」 2003優良電影劇本獎
- 《海角七號」2006新人組輔導金500萬元,2008 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,日本「亞洲海洋電影展」最佳影片首獎
連:魏導是從何時形成「要當電影導演」這樣的想法的?小時候是否就已經展露天份了?
魏:小時候完全沒有概念,我只是小學時候比較喜歡畫畫,每次畫都會拿到大小不一的獎項,所以常常被老師派去參加比賽。到小學五年級,我下了一個決定,我再也不要為了拿獎而畫,所以有好長一陣子,我都沒拿過畫筆。念電機專科的時候,知道這個技術不是自己喜歡的事情,但也還沒找到「自己喜歡什麼」。那時候台灣的男生,大專畢業都要去當兵兩年,那段日子唯一的好處,就是個緩衝期,可以想清楚未來要做甚麼。就在那段時間裡,認識了一個來自影視科系畢業的人,我跟他兩個人常常同班站衛兵,他會說好多影視圈的事情,那時候只是一個憧憬,覺得影視圈有很多明星會在你身邊穿梭不停。我那時只是覺得,影視圈是個有趣的行業。
知道規則才能打破規則
剛入行的時候,朋友拿到《無言的山丘》的分鏡本給我看,在此之前,我只看過劇本的格式,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分鏡本的形式。但我知道:這部片的王童導演是美術科系畢業的,圖畫得很好,那時電影剛下片不久,我去租錄像帶來看,試著畫場景的俯視圖,以及燈光、攝影機的位置,甚至是演員走位。我把每一場戲都拆解開來看,我才發覺到有一些像是臥室的戲,只有三個鏡位,但是鏡頭卻有很多種,然後透過剪接,就可以看到每個演員在那場戲中的情緒反應。那時甚至不知道所謂的”一百八十度假想線",也是因為這樣的練習,然後找人問,才知道拍電影有這樣的「潛規則」存在-知道規則才能打破規則,不是嗎?在做完這些場景分析之後,我又回頭去看了一次《無言的山丘》分鏡本,才發現到拍出來的其實與當初的分鏡本是有許多處不同的,分鏡本只能當成參考用。從畫出分鏡本,到拍攝電影、製作電影,到篩選畫面,到剪接,到最後成品出現,我第一次理解到,這樣的整個過程叫做「創作」。到這個時候,總算是對電影開了竅。
連:對一個新導演而言,指導演員演戲,尤其是專業演員表演,是一件困難的事情。魏導在這方面是如何下功夫的?
魏:我一開始拍前兩部短片的時候,只是把演員當成道具在使用,那其實是一種很不好的溝通模式。我那時也會怕跟專業演員溝通。後來跟著楊德昌學習,最後讓我理解了一件事:戲劇的主體還是演員。而且我發現,其實最容易溝通的反倒是專業演員,只要告訴他們你要的,告訴他們當下角色會有的情緒反應,專業演員通常都可以明白如何做。我自己也會預先想好每一場戲中演員的動作,在自己的腦海中有一個腹案,到了現場先請演員發揮,如果我認為不夠好,再把我想的方式提出來,這樣比較節省時間。等到讓導演幫演員設計動作細節的時候,那這個演員就不能稱為專業演員了。
連:除了楊德昌、王童導演之外有任何喜歡的導演或是影片風格影響著你嗎?
魏:沒有,完全沒有。我看電影很雜,如果有人推薦,我就看。我都是針對影片本身去觀賞,不會針對這是哪位導演的影片。再好的導演也會冒出爛片,再爛的導演偶而也會出現好電影。
連:我在網頁上看過許多對你的訪問,我發現你對於每一次的訪問都可以說出不同的故事,而且比喻都很精彩,你認為你是天生就會說故事嗎?
魏:我倒沒發覺這一點。不過有一件事情是亙古不變的:說書人需要觀眾,觀眾越喜歡聽,說書人講話越帶勁,到最後,因為觀眾捧場,說書人說著說著,還會唱起戲來…
連:談談《七月天》這部十年前講述少年成長的故事,影片裡面的氛圍是很壓抑的,找不到出口的一個灰暗的結局。怎會有這樣的劇本出現?因為這個故事跟之後的《海角七號》,那種勵志的感覺截然不同。.
魏:作品的內容跟作者當時的心態有絕大的關係。寫《七月天》那時候的心情就跟海角七號裡面的「阿嘉」一樣:看什麼都不爽,看什麼都不滿,都覺得老天對自己不公平,可是拍攝《海角七號》的時候情況更慘,但是卻有了一個信念:一定要把作品拍出來!所以,在《海角七號》裡面的劇情,每一個角色都有他們的任務,而他們最後成功了。
連:所以,《七月天》其實影射了整個大環境對你不友善?
魏:《七月天》那時其實是自我懷疑,入行已經一段時間了,我那時會常常想一個問題:一個人為了一個夢想,付出你的一切,到底值不值得?你想做,但是到底做得成還是做不成?我會不會變成離開家鄉工作,最後失敗回到故鄉成為酒鬼的那個人?我其實是把最壞、最悲觀的事情都放在《七月天》男主角「成家」身上。
《海角七號》是「非要到電影院欣賞不可」的電影
連:《海角七號》成為台灣電影史上最賣座的電影,導演對這件事情有沒有自己的看法?
魏:其實有很多台灣的觀眾告訴我,在這部片當中有七個角色,觀眾到電影院去觀賞時,好像都能在七個角色當中找到自己,從而覺得自己是電影中的一個角色。另外這部片應該可被歸類到「非要到電影院欣賞不可」的電影,這樣才能跟其他觀眾一起笑,一起有情緒的反應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有台灣觀眾到電影院欣賞達五次以上。
《海角七號》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任務,但是相同的是,他們都受過傷。現在社會上,一個人受了傷,誰會理你?可是把一群受過傷的人集合起來,那種集體爆發出來的力量是很可觀的。每個人的不滿、挫折、夢想都在《海角七號》裡面爆發。老實說:每一個角色,其實都有我的影子在裡面。
連:我們知道當初你要開拍《海角七號》的時候,很多人都不看好:沒有卡司、故事背景是大家不熟悉的南台灣,攝製成本是普通台灣電影的四到五倍,難道拍攝時都沒朝商業方向考量嗎?
魏:我在寫劇本的時候,只是回到一個「單純講故事」的心態,把一個故事給講好,然後再加入其他的元素:愛情、音樂、喜劇的橋段等等。但我覺得你越是迎合市場,你可能連自己當初創作的初衷都會失去。上帝創造人,一定是先塑一個形體,然後對著形體吹口氣。總不可能對著枕頭,對著茶杯隨便吹一口氣,對吧?用這個概念轉換到電影上,一定是先有一個成型的故事,給它一個主體價值觀,再發展其他的東西。
連:《海角七號》的故事線有兩條,其實這兩條線都可以單獨拍出電影來,當初為什麼要這樣設計故事?
魏:這其實是蓄意實驗自己對劇情的操控能力。《海角七號》甚至可說是我個人的實驗電影,我在這部片裡面不單單是練習劇情操控,我也試圖取得攝影(水中攝影以及日光夜景)、場面調度、視覺特效種種各方面的經驗。回到剛才的問題,兩條故事線也是希望豐富這部片的內容,但雖然是兩條線的故事,也要練習把故事說得很簡單。我想藉這部影片,試別人不敢試的。我希望每拍一部新片就能夠在各方面有新的嘗試,得到新的技能與體驗,才不會停留在原地打轉。
連:我們知道海角七號的故事是從「一封找不到收信人的信件」開始發想的,在這雙線的故事當中,是哪一個先開始的?
魏:一開始是想到一封寫著日據時代地址的情書,落到了一個年輕郵差身上。如果是老郵差取得這樣的一封信,肯定戲劇衝擊效果沒這麼好。既然是要找年輕的演員,我就在想:台灣電影圈還有合適的男演員嗎?不過,台灣的流行音樂卻是在華人音樂市場佔有領導地位,何況這部片跟音樂有直接的關連性,我就決定到流行樂界找演員。既然想到音樂,就想到恆春的月琴,我在勘景之後決定了恆春是這部片的主場景,之後的故事就很順利地,一個接著一個開展了。
連:《海角七號》裡頭有七個角色,剛才魏導說到每個角色都有賦予不同的任務,這些角色來自不同的地方,然後匯集在一起。這是否意味著每個角色都有一個對應的方向?或是對應的族群?
魏:在恆春那個地方,有客家人、閩南人,然後有月琴,月琴就可以聯想到彈奏者是個老人;接著想到的是當地沒有出遠門,還在上學的小孩。客家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勤奮的工作態度,所以有客家的業務員。再來就是原住民,台灣的原住民一般的出路是考公職,當老師、公務員或是軍人警察,所以戲中會有一個原住民警察;再來我希望有個藍領階級,因此出現了修車工人。還有就是到墾丁觀光的外國人,以及到墾丁開飯店的財團。就這樣,把墾丁那裡會出現的族群都湊齊了,其實也就是把台灣島上各種人群都湊齊了。
連:我覺得這部片中充滿了「衝突的美感」。像是那個鎮民代主席,外表行事跋扈,卻又能說出「這片海這麼美,為什麼留不住年輕人」如此浪漫的話;又如喜宴搭棚請客那場戲中,修機車的水蛙對老板娘的感情雖不合道德規範,卻是真情流露;最後眾人不約而同漫步到海邊等待天亮。你一方面呈現台灣的雜亂衝突的生活場景,又讓角色存在小奸小惡的行為,卻極具企圖凸顯這些小人物心中真與美的一面,甚至是無可救藥的浪漫;不知道魏導心目中是否有特別的美感觀點?
魏:其實我覺得這個樣子是一種「台灣式的思考」,大家看台灣人可能只看表象,看到這個人粗俗的言語或是動作,卻看不到他內心的溫柔。鎮民代表那個角色的原型其實是我父親,我父親並不是政治人物,他把自己定位是「漁夫」,有自己的一艘小漁船,他也有他脾氣不好的的一面,平常不高興就開罵,但是當我母親要我父親出面講一句話以平息爭端的時候,他反倒不想講。他覺得在節骨眼上不應該講太多的話讓別人討厭。我父親知道我在拍片,有一次在喝了幾杯小酒之後,我父親就問我:「這片海這麼美,你們拍片的人為什麼不會想來拍這片海?」這也就演變成各位觀眾在電影裡面聽到的台詞。父親每天去抓魚,我想他是喜歡上那片海洋才會每天去抓魚。其實台灣的男人都是很浪漫的,只是浪漫被壓抑住了。假如去研究台灣歷史上的男人,不管漢人,原住民,都是浪漫的。浪漫的人才會去當海盜,才會冒險想要找到新天地;浪漫的人才會想要到山裡面跟動物在一起。我甚至覺得浪漫是男人的天性,女人只是在外表上的浪漫,而男人的浪漫會產生開闊的天地。
連:彩虹會是你用來當成「作者論」的標記符號嗎?
魏:絕對不會。
我是在拍攝《賽德克巴萊》五分鐘短片之前,得知賽德克族人有個「死後走過彩虹橋去見祖靈」這樣的傳說,之後我在構思《海角七號》的時候,為了如何讓兩個時代的故事可以連結在一起而傷透了腦筋,如果到電影結尾才發生,這個連結會顯得很薄弱。想了好久,最後才想到彩虹:不同時代的戀人,他們看到的彩虹,顏色相同,形狀也相同。當我把彩虹放入劇中之後,我開始察覺彩虹可以被賦予意義:彩虹有七個顏色,每個顏色都很明顯,但是可以相互包容。從這樣的出發點,然後擴大思考,彩虹就有了全新的意義與靈魂,成為這部片要表達的重要象徵。
連:音樂的應用在《海角七號》是很成功的,可不可以談論一下這個部份?
魏:因為這部電影有兩條故事線,所以一開始思考音樂的時候也是兩條軸線。不過,製作初期就已經決定《野玫瑰》是片尾曲,所以我就要求音樂創作者,出現情書時的背景配樂必須可以銜接上《野玫瑰》,<野玫瑰>之後也能銜接上主題音樂,然後還可以連接到老太太拆開看信,這個部份就是主旋律了。另外的思考在於情緒的表達程度:如果某個畫面的情緒渲染力不夠,就要靠音樂釋放更多的感覺。舉個例子,友子在沙灘上漫步,我必須要跟音樂創作者溝通,節奏必須要跟著友子的步伐速度走,然後我再指定「音樂揚起」的點。老阿嬤看信也是一樣,我也設定音樂在阿嬤回頭的時候,音樂必須揚起。很多的時候,只要音樂對準的畫面上的某一點,觀眾的情緒就會被挑起。
連:在電影還沒上映以前,魏導是否有設定過這部片的最大票房以及影響力?有沒有想過這部片推出之後的「最壞狀況」?
魏:其實一開始就預設會虧錢。由於跟戲院有拆帳關係,票房必須達到一億新台幣才能打平。誰敢想一億的票房?我預設在台灣的票房大約是三千萬到五千萬新台幣,我就算贏,超過新台幣五千萬就算大成功。至於海外的票房,當初是有想過,但前提一定是要「引起海外好奇」,台灣市場必須大賣,這樣才有話題性。至於對這部片最壞的想法,頂多就是不賣,虧錢,但我仍相信《海角七號》這部片的品質不錯,我仍然會有下一次的拍片機會,只是案子的大小,不知道。
連:台灣電影創作者跟台灣觀眾之間似乎存在著隔閡,每一次創作者把他們自認為的好作品推向市場,但大多鍛羽而歸。請問你是如何有這樣的自信,確認自己的電影是個市場會接受的東西?
魏:我自認《海角七號》是一個好劇本,而且我說了一個好故事,但是說真的,我那時還是不知道觀眾是否會買帳,我只能把我份內的事情做好。
連:從導演非要找到三胞胎來演戲談起,想必導演必定是「劇本如何寫就要如何拍」,請問在《海角七號》裡面,是否還有劇本寫了但卻沒有做到的地方?
魏:劇本裡面寫到的,都做到了,只是有些沒有做好。但我在前面有提到,這部片有許多帶有實驗精神的事情,包括模型攝影、試驗台灣的視覺特效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等等。我拍完這部片,了解台灣還有許多技術方面可以加強的,畢竟台灣電影積弱已久,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趕上的。
連:在《海角七號》當中,魏導有些橋段細節處理得非常好。魏導是否會有把想到的橋段給記錄下來的習慣?
魏:以前曾經有過,但總是忘記得多,記得的少,以後就乾脆不去記了。我想強調「認真生活的重要性」,有些創作者總是一個人窩在家中,看錄像帶、看書,我覺得那是虐待自己。我自己的定性不夠,沒辦法待在書桌前面超過三小時,三個小時已經是極限。寫作兩個小時,我大概就要出外走走,吃個東西犒賞自己。我劇本裡面的橋段,都是生活經驗而來。
連:《海角七號》在國外參展,導演是否有聽見任何特殊的評論或是看法?
魏:其實都是台灣的觀眾理解的比較多,外國的觀眾都很友善,該笑的地方都有笑,大多的回應是「我們看得懂你要表達的」。
回到矛盾與衝突的原點,才能化解現有的矛盾與衝突
連:我們知道魏導在其他的媒體上提到,下一部片要拍攝《賽德克巴萊》,最後希望完成的是《倒風內海》三部曲。魏導如何能夠如此地篤定自已以後要做的事情?
魏:這裡要更正一下說法:下一部要拍《賽德克巴萊》是沒錯,但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為了要完成我的夢想,中間還需要經歷許多轉折,走更多迂迴的路,或是接拍其他的案子。換個角度說:如果可以完成《倒風內海》三部曲,那麼我就不會再拍了。《倒風內海》是一本記述西元一六二四年台灣歷史的小說,有漢人、原住民、荷蘭人。小說內原來的觀點只有台灣的平地原住民西拉雅族,我打算把這一個故事用前面三種觀點,開拍成三部片。這三部片如果能夠成功拍完,大概就是我的極限了。
連:怎會想要開拍《賽德克巴萊》的故事?
魏:一開始只是從電視上看到原住民上街頭抗議,覺得原住民似乎無力抵抗社會的改變,但我依稀記得:原住民是曾經對抗過日本人的!最重要的事件是「霧社事件」,還有一位領導事件的原住民莫那魯道。隔天我去書店查找資料時,才發現這個故事的寓意浩大。原住民曾經有過的光榮歷史,可是有許多原住民自己都忘了。過去大家都是用漢人的觀點看待這個抵抗日本人的事件,我希望用原住民的觀點重新詮釋。
連:《賽德克巴萊》與《倒風內海》被你列為這一生中一定要完成的電影,為什麼你會把拍台灣的歷史故事看待得如此重要?
魏:應該說是一種「拿到族譜的心情」。有些人家裡可能會有祖先留下來的藥方帖子,或是點穴圖;有些人可能家中會有祖先留下的遺物,但我沒有。可是如果有一天回家,家裡面告訴你,族譜找到了,你可以想像那種心情嗎?魏姓的家族最早是從山西,然後因為戰亂遷到江西,又從江西到閩西,然後遷台。族譜上寫著來台開基魏氏先祖的名字,最後是我的名字,我太太的名字以及我小孩的名字。我在三十歲左右拿到這本族譜,當下就掉了淚。那是一種發現自己身世的感動,我希望觀眾也能夠體會我的心情,關心我們居住的土地上,過去曾經發生的歷史事件,而這些歷史事件,其實是跟你的血緣有關係。
另外一個想法是台灣社會上有許多的衝突與矛盾,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歷史因素造成的。台灣劇烈的變動被壓縮在四百年內:荷蘭人、鄭成功、原住民、清帝國、日本人、國民政府,戰亂跟殺戮接連不斷,這是台灣歷史最獨特的地方,也是台灣社會衝突與矛盾的根源。倘若僅僅了解單一族群的歷史觀點,不免偏頗。唯有從宏觀的角度了解台灣歷史,回到矛盾與衝突的原點,才能化解現有的矛盾與衝突。歷史本來就是個循環,在愛與恨之間相互交錯,台灣島上的人民應該感受特別深刻。比方說,你爺爺殺了我爺爺,我恨你;往上一代查,原來是我的先祖有愧於你的先祖;再往上查,又查到了如何如何…。照這樣查找到最源頭,最後查到了最源頭的一棵樹與一顆石頭,這兩者又是如何開始產生仇恨與矛盾的?所以我認為唯有回到原點看事情,才能讓各個族群彼此相互尊重。我自認我有著宏觀的歷史角度,但卻常被人用錯誤的政治角度解讀,這是我比較遺憾的。
歷史是不能遺忘的,但是可以被原諒。回到歷史原點看待歷史,繼而各族群相互尊重與理解,接著才能攜手合作,創造未來。所以《賽德克巴萊》是為了要化解原住民與日本人之間的仇恨,另外還有一個案子,是希望化解國民黨、共產黨之間的仇恨-兩個政黨的最源頭只是哲學上的理念不同,理念的不同造成不同的政黨,一開始只是相互競爭理念,但最後卻造成內戰。這個國共內戰的故事不會是我拍,但是我會參與策畫。
我還是想要強調一點:不要因為我化解了某些族群的仇恨,而造成其他族群對我的另眼看待。這絕不是我的本意。也不要因為我的電影裡面有一句罵台北的話,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件,就特別猜測我的立場。我現在還住在台北呢!
連:魏導在哲學或歷史上的看法,似乎超越了一般人的水平。魏導喜歡看書嗎?
魏:其實只是單純因為要寫劇本而看書,像《倒風內海》的故事也是因為當時候要蒐集《賽德克巴萊》的資料到書店去,不經意地看了《倒風內海》這本小說,而為了要寫好故事,你一定會去蒐集更多當時候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的資料,甚至是要看看事件的前十年,後十年發生了甚麼事。就這樣不斷的收集資料之下,建構自己的劇本空間。我純粹只是為了要寫劇本而看書。
連:宗教信仰對你生活上態度或創作的關係?
魏:我是個第三代的基督徒,從小就信仰基督教,對信仰也經歷過叛逆期。這些叛逆到現在為止並沒有被壓抑下來,反倒是在我看了許多歷史的書籍之後,讓我對宗教信仰變得宏觀-沒有什麼是不行的。例如說:基督教不可以拿香,那我「鞠躬」總可以吧?基督教不可以拜祖先,那我追思先人總可以吧?那些只是一個儀式,傳統的信仰只是告訴你「不行」但是沒有告訴你「原因」。基督教不拿香的是因為「不可以拜別的神」,我們以前總是用「行為」改變「觀念」,我們現在應該用「觀念」改變「行為」。
連:魏導以前還沒拍《海角七號》以前被人稱「小魏」,現在被人稱為「魏導」,這其中你的心態有甚麼樣的變化?
魏:我還是喜歡大家叫我「小魏」。喊「魏導」好像就不可以聊天了。
連:魏導覺得大陸跟台灣有無任何電影交流與合作的機會?
魏:以現階段而言,大陸電影要到台灣來通行無阻,例如《集結號》也在台灣的戲院放映過;但台灣電影要到大陸去,審批作業還是很複雜。我自己的構想是從交流觀摩開始:每年選十部台灣電影以及十部大陸電影,到台灣辦大陸影展,到大陸辦台灣影展,在每一個城市巡迴放映。但我不知這樣是否會牴觸大陸的法規?或是把放映地點改到學校,辦理台灣影展,當成是文化交流活動。文化的互動是可以走在合作之前。電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,無論是文盲、高級知識分子,都可以透過易懂的影像了解彼此,然後再談合作。
連:給「下一個青年導演」有何建議?
魏:我也還算是青年導演吧!我認為每個人在釋放能量時,還是要多吸取養分,所以,多看書吧。